到北宋年间,在唐代处于低谷状态的文人琴,因为一个著名的文人集团而再行崛起,形成中国文人琴的又一高峰。代表人物有范仲淹、欧阳修、苏轼等。这个文人集团所振兴的文人琴,是揉合了儒家、道家和禅宗的思想,再一次宣示了文人琴的独特理念和情趣。如范仲淹,是诗人、政治家,曾自谓其学琴“诚不敢助《南薰》之诗,以为天下富寿;庶几宣三乐之情,以美生平”(《与唐处士书》),明显属于道家、禅宗一路的。“范文正公酷嗜琴,而平生所弹只《履霜》一操,时人谓之‘范履霜’。”(《诚一堂琴谱·琴谈》)弹琴不以技巧为尚,不以悦人为务,也不以多少为要,而是注重修身理性,自得其趣,正是文人琴的基本观念。正因为此,同为文人琴家的朱长文对范仲淹特别赞赏:“君子之于琴也,发于中以形于声,听其声以复其性,如斯可矣。非必如工人务多趣巧,以悦他人也。故文正公所弹虽少,而得其趣盖深矣。”(卷五)文人琴的最有代表性的琴家还是欧阳修,他的许多自述正表现了这一点:“余自少不喜郑卫,独爱琴声,尤爱《小流水》曲。平生患难,南北奔驰,琴曲率皆废忘,独《流水》一曲梦寝不忘,今老矣,犹时时能作之。其他不过数小调弄,足以自娱。琴曲不必多学,要于自适。”(欧阳修《三琴记》)又说:“予尝有幽忧之疾,退而闲居,不能治也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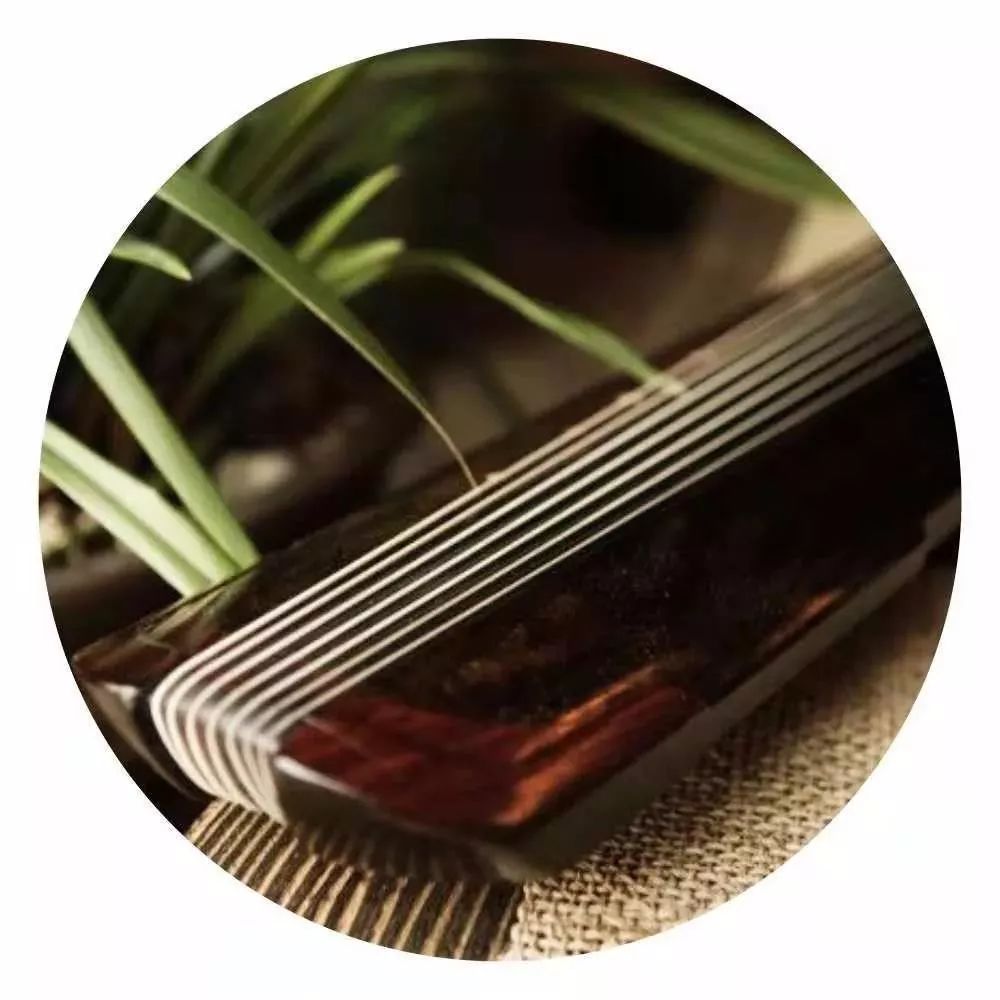
既而学琴于友人孙道滋,受宫声数引,久而乐之,不知疾之在其体也。”(欧阳修《送杨置序》)又有诗云:“吾爱陶靖节,有琴常自随。无弦人莫听,此乐有谁知?君子笃自信,众人喜随时。其中苟有得,外物竟何为?寄意伯牙子,何须钟子期。”(欧阳修《夜坐弹二首》)这里所特别强调的自得、自适,无关他人、亦无关形迹的琴艺观念,正是文人琴的。他在另一首诗中还对传说中琴的神秘效果和非凡力量表示怀疑,使琴的品格更趋平易,更近人情:“钟子忽已死,伯牙其已乎?绝弦谢人世,知音从此无。瓠巴鱼自跃,此事见于书。师旷尝一鼓,群鹤舞空丘。吾恐二三说,其言皆过欤?不然古今人,愚智邈已殊。奈何人有耳,不及鸟与鱼?”(欧阳修《夜坐弹二首》)文人琴重在自娱,故而对那些十分夸张地描写琴的影响力的做法,自然会持怀疑的态度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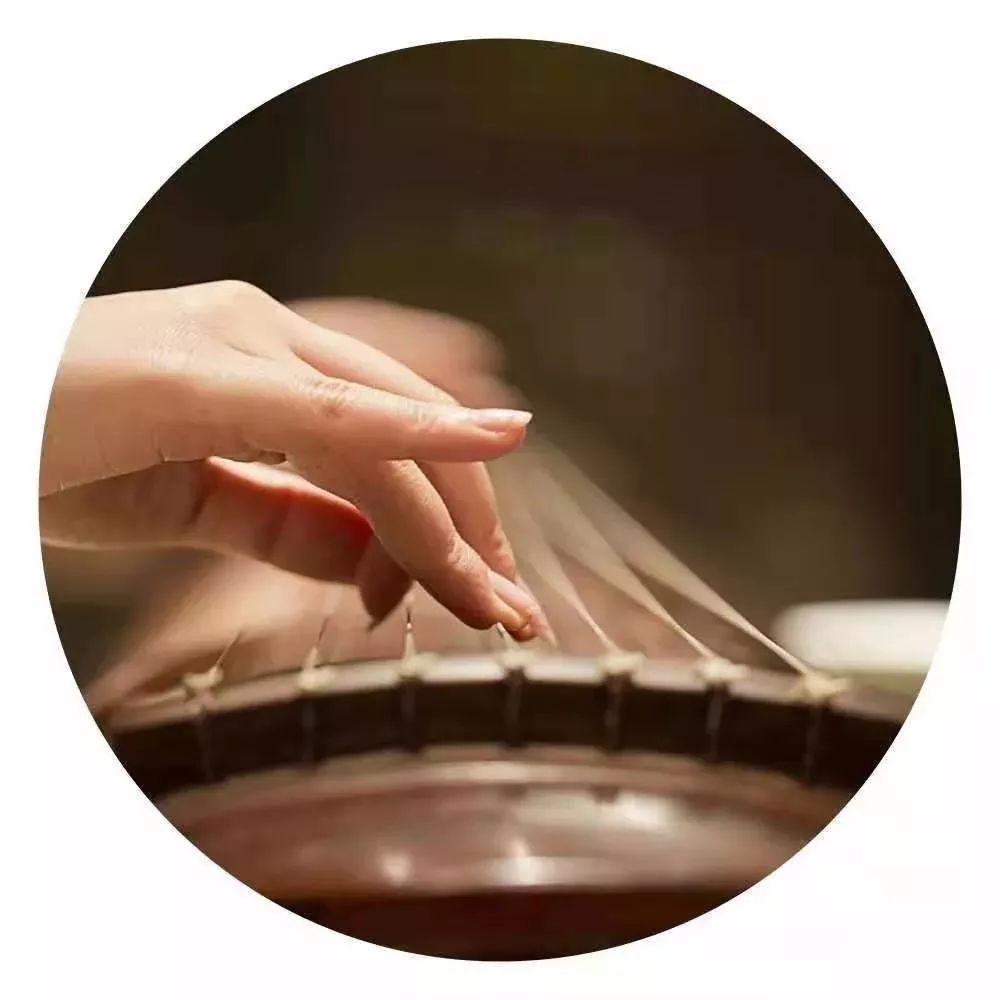
与此同时,艺人琴在北宋也涌现出一批琴家,占据着宋代琴坛的另一半江山。稍微不同的是,北宋的艺人琴,主要是由一批僧人琴家充当的,其主要代表有:朱文济、夷中、知白、义海、则全和尚等。朱文济是太宗时朝廷琴待诏,“性冲淡,不好荣利,唯以丝桐自娱,而风骨清秀,若神仙中人”(卷五);以琴名于当世,被称为“鼓琴为天下第一”(沈括《梦溪笔谈·补笔谈》)。朱文济不是僧人,但他所传著名弟子几乎都是僧人,成为北宋琴坛一道别致的风景。朱文济所传的琴僧是慧日大师夷中,夷中又传知白和义海,义海又传则全和尚,则全又传僧照旷。其中知白、义海和则全最为著名。欧阳修曾写有听知白弹琴诗,诗中有介绍其琴艺的诗句:“遗音仿佛尚其变,何况之子传其全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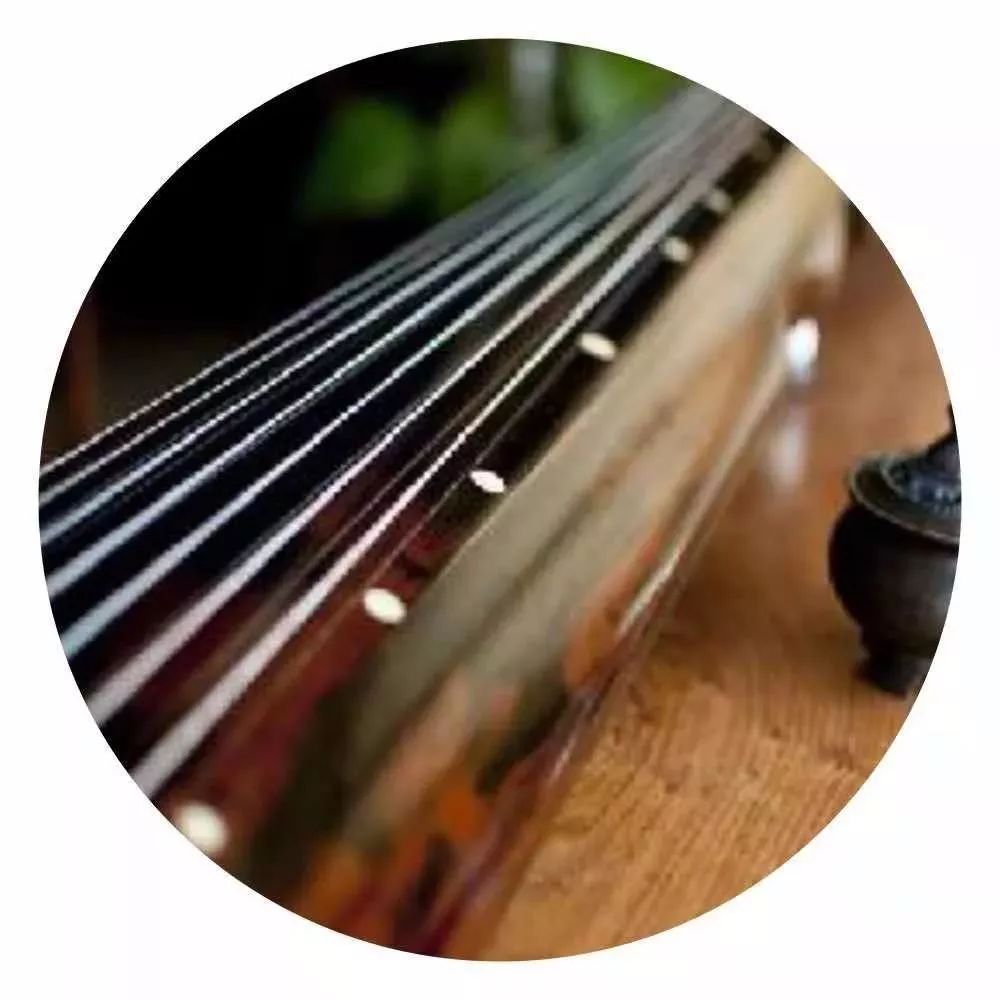
孤禽晓惊秋夜露,空涧夜落春嵓泉。……岂知山高水深意,久以写此朱丝弦。酒酣耳热神气主,听之为予心萧然。”(《送弹琴僧知白》)关于义海,沈括《梦溪笔谈》记云:“京师僧慧日大师夷中……以授越僧义海,海尽夷中之艺,乃入越州法华山习之,谢绝过从,积十年不下山,昼夜手不释弦,遂穷其妙。天下从海学琴者辐辏,无有臻其奥。海今老矣,指法于此遂绝。海读书,能为文,士大夫多与之游,然独以能琴知名。海之艺不在于声,其意韵萧然,得于声外,此众人所不及也。”(《补笔谈·故事》)则全和尚则对义海的琴论加以发挥,撰有《则全和尚节奏指法》,对演奏艺术作了独到的探讨。这几位琴家虽为僧人,但从其高超的演奏效果、刻苦的钻研精神和精细的技法追求等方面可以看出,他们实际上已经成为专攻琴艺的艺人琴家了。
两个旗鼓相当的琴人群体——文人琴群体和艺人琴群体同时屹立北宋琴坛,实在是千载难逢的壮景。但一开始,他们就显示并表述了自己独特的琴学理念,形成两股并行且又不无对峙的张力。
文人琴在其刚出现之时就明确表述了自己的琴艺观念,那就是范仲淹的“琴不以艺观”的思想。他说:“盖闻圣人之作琴也,鼓天地之和而和天下,琴之道大乎哉!秦作以后,礼乐失驭,于嗟乎,琴散久矣!后之传者,妙指美声,巧以相尚,丧其大,矜其细,人以艺观焉。”(范仲淹《与唐处士书》)显然,范所推崇的是上古的、也是理想中的圣人之琴、中和之琴,而反对后世传者的“妙指美声,巧以相尚”,反对将古琴当作“艺”来对待。实际上,范仲淹所反对的这种琴艺,就正是艺人琴,特别是唐代以来的艺人琴。这个观念影响极为深远,直到现在,仍有不少人在复述着这个命题,坚持古琴不是乐器、琴乐也不是音乐的观点。

欧阳修也主张“琴之为技小矣”,认为只有当技艺表现出“忧深思远则舜与文王、孔子之遗音”,“悲愁感愤则伯奇孤子、屈原忠臣之所叹”,且“道其堙郁,写其忧思”时,方能称之为“至者”(《送杨置序》)。他的另一首诗:“弹虽在指声在意,听不以耳而以心。心意既得形骸忘,不觉天地愁云阴”(欧阳修《赠无为军弹琴李道士》),表达的亦是文人琴轻声而重意、轻技而重心的思想。无独有偶,他的学生苏轼也有一首诗:“若言琴上有琴声,放在匣中何不鸣?若言声在指头上,何不于君指上听?”(苏轼《题沈君琴》)同样是轻声而重意,轻技而重心。文人琴对于自己的琴音、琴艺也有自己的追求,这个追求是由范仲淹的前辈琴家崔遵度说出、又由范予以发挥的。范仲淹在一封信中记述了这次谈话的内容:“某尝游于门下,一日请曰:‘琴何为是?’公曰:‘清厉而静,和润而远。’某拜而退,思而释曰:清厉而弗静,其失也躁;和润而弗远,其失也佞。弗躁弗佞,然后君子。其中和之道欤?”(范仲淹《与唐处士书》)
与之不同,艺人琴家则走着一条由技到艺的琴乐道路。在他们的意识中,琴首先是乐器,它要演奏出音乐,其音乐必须是艺术。这是以“艺”待琴。也正因为是艺术,是乐器,故而必然首先解决技巧问题,必然花费大量精力钻研音乐形式的规律。上述几位僧人琴家就是在这些方面一点一滴地做起来的。夷中、知白、义海,因为没有留下文字著述,不能直接了解其对形式、技术的观点,但从他们举世公认的高超琴艺,便不难想象他们那刻苦追求、长期磨练的情景,一如义海大师的“谢绝过从,积十年不下山,昼夜手不释弦”(沈括《梦溪笔谈》)的功夫之类。此外,我们还可以从则全和尚所写的《节奏指法》之类的书中窥其一二,在那里最清楚地记录了艺人琴家们最关心的问题和最用心的课题。例如,关于弹奏不同类型曲子(品、调、曲)时应注意的要领,《节奏指法》就作了如下精细的辨析:“凡弹品则全与调子不同,要起伏快。今人弹调子往往如操弄,不知节奏故也。凡弹调子如唱慢曲,常于拍前取气,拍后相接。弹调子者每一句先两声,慢,续作数声,少息,留一声接后句,谓之双起单杀。凡弹操,每句以一字题头,至尽处少息,留两声相接后句,与调子相反。学者若能晓此三事,则品调曲自能分别也。”(据《琴苑要录》)这个工作,文人琴家一般是不会做的。这就是不同。
文人琴与艺人琴的这个不同,我们可以通过一件琴史上的著名公案见出,那就是对韩愈《听琴诗》的不同理解。
韩愈曾写有《听颖师弹琴》诗:“昵昵儿女语,恩怨相尔汝。划然变轩昂,勇士赴敌场。浮云柳絮无根蒂,天地阔远随飞扬。喧啾百鸟群,忽见孤凤凰。跻攀分寸不可上,失势一落千丈强。嗟余有两耳,未省听丝篁。自闻颖师弹,起坐在一旁。推手遽止之,湿衣泪滂滂。颖乎尔诚能,无以冰炭置我肠!”从这首诗的内容可以看出,颖师是一位典型的艺人琴家,技法娴熟、高超,注重音乐表现的内容,注重音乐的感染力量,而且做得十分成功,诗人已完全被他俘虏。
但是,对韩愈的这首诗,历史上却产生过争论,形成两种完全对立的意见。争议是由欧阳修的话引起的,欧阳修认为这首诗不是弹琴诗而是弹琵琶诗。见于苏轼的《琴书杂事》:“‘昵昵儿女语,恩怨相尔汝。划然变轩昂,勇士赴敌场。’此退之《听颖师琴》诗也。欧阳文忠公尝问仆琴诗何者最佳,余以此答之。公言:‘此诗固奇丽,然自是听琵琶诗。’余退而作《听杭僧惟贤琴诗》云:‘大弦春温和且平,小弦廉折亮以清。平生未识宫与角,但闻牛鸣盎中雉登木。门前剥啄谁扣门?山僧未闲君勿嗔。归家且觅千斛水,净洗从前筝笛耳。’诗成欲寄公而公薨,至今以为恨。”(《欧阳公论琴诗》)在这个问题上,苏轼是赞同欧阳修的看法的。
后来有人以此诗问义海,义海回答说:“欧阳公一代英伟,然斯语误矣。”接着便对原诗逐句加以解释,指出它不是弹琵琶诗,而正是弹琴诗。他说:“‘昵昵儿女语,恩怨相尔汝’,言累柔细屑,真情出见也;‘划然变轩昂,勇士赴敌场’,精神余溢,竦观听也;‘浮云柳絮无根蒂,天地阔远随飞扬’,纵横变态,浩乎不失自然也。‘喧啾百鸟群,忽见孤凤凰’,又见脱颖孤绝,不同流俗下俚声也;‘跻攀分寸不可上,失势一落千丈强’,起伏抑扬,不主故常也。”逐一指出韩诗中的各句都分别是对一个特定情境的刻画,或是对一种技法效果的描写,且都是只有琴声才可能具有的妙处,“琵琶格上声乌能尔耶?”他的结论是:“退之深得此趣,未易讥评也。”问者还以苏轼的《听杭僧惟贤琴诗》问义海,义海也回答说:“东坡词气倒山倾海,然未知琴。”接着也同样逐句加以分析:“‘春温和且平’,‘廉折亮以清’,丝声皆然,何独琴也?又特言大小弦声,不及指下之韵。‘牛鸣盎中雉登木’,概言宫角耳。八音宫角,岂独丝也?”闻者都以义海为知言。(均见《西清诗话》)

对韩诗的两种不同看法,实际上根源于两种不同的琴艺观,即文人琴与艺人琴对琴的不同理解。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:(1)对琴乐本质的看法,即琴乐的本质究竟仅仅是中和还是对自然人生的表现。欧阳修等文人琴家认为琴是中和之音、大雅之器,故而不应有促节繁声的音调出现;义海等艺人琴家则首先理解琴乐为对自然人生的表现,不同的自然事物和不同的人生情境就会有不同节奏的音调出现。琴与琵琶的差别,实际上源自对琴乐本质的不同理解。(2)对琴乐形态的态度,即琴乐的形式、技法等形态在其音乐表演中居有什么样的地位。以欧、苏为代表的文人琴是认琴乐为修身养性的工具,演奏的效果又全在自己的感受,是自得、自适、自娱、自乐,故对音乐的形态并不多加注意,更不会用心去考辨,认识也就自然粗疏;而以义海为代表的艺人琴家则首先是把琴作为乐器,是演奏乐曲、打动听众的工具,故而必然对音乐的形态特征精心钻研,且有着长期的实践,辨识当然精微。从这件事情中,我们也可看出,文人琴与艺人琴之间的差异是多么大,对立是多么深。
当然,我们指出宋代文人琴与艺人琴的差异和对立,并不意味着两者在根本上不可调和,也不意味着它们完全是南辕北辙,毫无共同之处。实际上,它们总是有着各种天然的联系和共同的基础,虽然有些方面正好相反,却又往往是形成互相需要、互相欣赏、互相补充的必要条件,也是后来(明清时期)走向交流融合的内在动力。即以北宋的这两大琴统而论,它们也存在着互相交流和欣赏的事实。例如欧阳修,他对慧日大师夷中的琴艺早生向往之心,但一直无缘相见。后有幸遇到他的弟子知白,聆听了他的精彩演奏,十分欣赏。还纪诗一首,真实地写出自己长久的心愿终于实现后的欣慰和满足:“吾闻夷中琴已久,常恐老死无其传。夷中未识不得见,岂谓今逢知白弹。遗音仿佛尚其变,何况之子传其全。”最后还描述了自己听琴时的真实感受:“岂知山高水深意,久以写此朱丝弦。酒酣耳热神气主,听之为予心萧然。嵩阳山高雪三尺,有客拥鼻吟苦寒。负琴北走乞其赠,持我此句为之先。”(欧阳修《送弹琴僧知白》)这里,作者对琴家的钦佩之情已溢于言表,情真而意切。实际上,北宋文人琴家经常与一些僧人、道士及僧道琴家交往,这其间自然免不了琴艺的交流和互赏。譬如苏轼就与法真等僧人琴家和崔闲等道士琴家来往密切,甚至还有过音乐上的合作(如为《醉翁吟》谱曲)。

【子曰:君子和而不同。所谓文人琴和艺人琴,是两个不同的群体对古琴认知上的差异。虽然观点不同,但正是因为存在这种差异,才促进了古琴在琴曲创作、琴技探索、琴学思想、古琴美学等方面研究走向更深的领域,两者相辅相成,缺一不可。古琴之美,在于古朴醇和的音色和丰富的琴曲表现,亦在于中正平和、天人合一的琴学思想。少了哪一个,就成了缺手断脚的木偶,会被历史所抛弃。】
完

